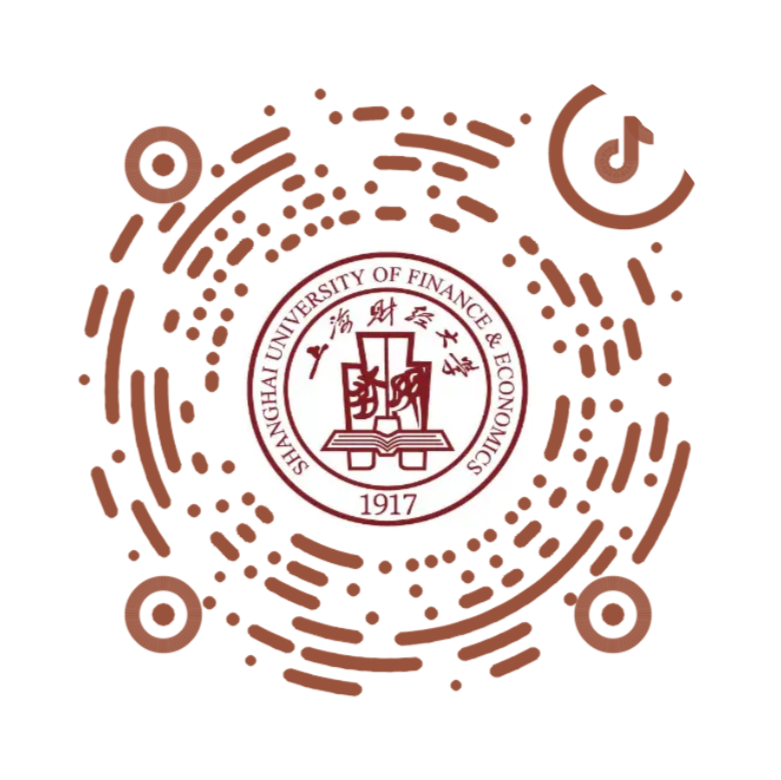张牧扬
最近两年,我国的经济增速从先前的平均9%以上回落到7%左右,以名义价格计算的财政收入增幅更是大幅度回落,从2013年以前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2014年和2015年的8.6%和8.4%。这其中既有经济放缓、企业利润下滑的因素,也有结构性减税的因素。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中央和地方部门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却发现财政心有余而力不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
近来,包括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都提出了提高财政赤字上限的建议。2015年,我国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和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于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3%的要求还有较大的空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财政赤字率提高至3%,财政赤字规模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此前还表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的警戒线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以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有效进行逆周期调控,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并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
我们来考察一下国际上主要国家的财政赤字和财务情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对26个发达国家和27个发展中国家2016年度到期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预测中,我国的到期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分别占GDP的1.8%和2.2%,两者之和在27个发展中国家中仅高于智利和秘鲁两个国家,单看财政赤字率,也仅高于智利、印度尼西亚、秘鲁、罗马尼亚、泰国和土耳其六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到期政府债务率和财政赤字率之和也仅高于瑞士和韩国。从这一意义进行国际比较,我国的到期政府债务率和财政赤字率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对于赤字率提高的政策效果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分清赤字率的提高是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权宜之计,还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因为财政赤字需要通过发行债券进行筹资,赤字率的上升对应的是政府负债率的同步上升。如果提高赤字率是暂时的,会通过若干年后的财政盈余来补助,意识到这一点的纳税人会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额外税收,使得可支配的财富与征税的情况一样。因此,在减税或者增加刺激政策的同时暂时提升赤字,其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那么,如果长期提高赤字率呢?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直到变得不可持续,从而造成巨额的债务负担,甚至产生经济危机。化解高额债务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借新还旧,其二是期望未来经济增速提升,通过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债务率。第一个方法在长期维持低利率、低通胀且货币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适用,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然而即便是日本,也难免受到债务累积的拖累。日本政府负债在2013年底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在2015财年的日本政府预算中,用于还本付息的支出就达到234.6万亿日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24.3%,其中仅利息一项支出就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10.5%。尽管2014年4月将消费税税率由5%提高至8%的政策已经对消费造成了冲击,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于2017年4月起将消费税进一步提高至10%,以降低财政赤字,也属无奈之举。第二个方法需要建立在对于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期之上,一旦这一预期落空,容易导致债务危机,典型的例子是巴西。2013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巴西的债务率一直保持在50%—60%之间,赤字率低于3%。除了2009年短暂地出现负增长之外,巴西经济增速在2011年以前均保持在5%—7%的中高速水平,因此其债务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并没有暴露。2012年以来巴西经济增速由5%以上逐步下滑至0附近,债务问题便露出水面:2015年的财政赤字率超过了10%,债务率也上升到了66%。当年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通胀率超过10%,货币相较2009年贬值了50%以上。经济和债务危机使得巴西经济2016年的前景变得灰暗。
那么,我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2014年8月31日修订的《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不列赤字”,因此,我国的财政赤字只存在于中央政府,一直以来也控制得较为妥当。政府债务方面,《预算法》规定,“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必需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举借债务应当控制适当的规模,保持合理的结构”,对于地方政府负债,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在这些严格的规定之下,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由2012年的32.5%升至2015年底的40.6%。尽管这一比例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很高,但这一数字只包括了中央政府的债务和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包括各类由地方政府实际营运或担保的城投债和各类融资平台。由于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政府债务的最终担保人仍然是中央政府,因此实际的债务会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这一现象通过近两年地方债置换发行的密集度可见一斑。
因此,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财政赤字率提高至3%以后,赤字率是否存在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是需要作出权衡取舍的。通过提高赤字率给私人部门减轻税负,同时不减少政府支出,短期内可以在起到稳增长的效果。但要真正实现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今后如何通过政策的调整将赤字率调整回较低的水平,使得政府债务不会滚雪球似的累积,避免出现经济“日本化”或者“拉美化”,需要决策层的智慧和勇气。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