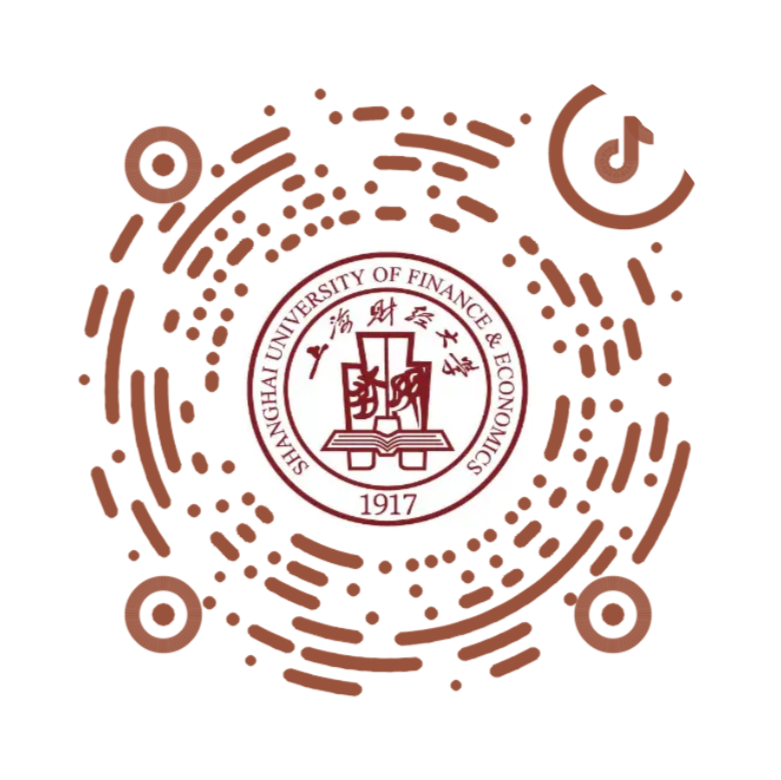本报首席记者 徐瑞哲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租还是先有税?”在上海财经大学近日一堂《经济中国》思政课上,年过六旬的黄天华教授弓着背发问,转身在黑板上写下“禾木旁”:它们都来自粮食。
财政从何而来,从原始社会起,上下五千年。而黄天华用了他生命长度的将近一半,写就500余万言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今年9月即将出版多卷巨著,兑现了他当年“中国人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同时,与此相关的百余万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一稿也已完成,并正筹划200万字的《中国军费制度史》。
书稿一张张地累积,他1.8米的身形,却仅剩107斤的体重;事关“金钱”的基础研究,他自费投入入不敷出,只买赴京最便宜的火车票;身在财经热门高校,他偏偏选择冷门史学,副高级职称评了8次才过。
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黄天华正在出版的 《中国财政制度史》扉页上就醒目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
他生于上海,进车间工作,高考恢复后考入原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后有一段财政机关经历,之后又回校任教。当上世纪80年代,黄天华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研时,他遇见了改变自己人生走向的东北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马大英。有一天,马老师对他说:“对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远远超过了我们!”
黄天华颇感震惊。原来,关于唐代经济和财政制度的研究,第一中心在日本,第二中心在美国;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则在巴黎、东京;而研究中国清朝、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文献史料,绝大部分存于美国。
历史怎么走错了房间?中国人研究自己的财政问题居然没有“入场券”?“小黄,搞历史很苦的,”马老师接着说,“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
风华正茂的黄天华,毫不犹豫答道:“马老师,您放心,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而今,他才知此话过于乐观,以至于此后好几次陷入绝望。
黄天华记得,在一次全国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曾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财税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密切关联,财政制度史研究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所需史料几乎穷尽古代典籍,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黄天华给大学生上的课,关于“租税合一”,就是把《说文解字》翻了个烂熟。
为了找到第一手资料,黄天华请所在学院的外籍院长从美国杜克大学大量复印原始文献,近千份材料都是汉字所写,但国内从未印过,这种感觉很不是滋味,令他无法释怀。
小时候,黄天华喜欢一首老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告诉记者,当孩子大了,请妈妈坐下,又如何给她讲过去的事情呢?“如果美国人、日本人来讲,祖国妈妈多少是失望的。”黄天华语重心长地说,“尽管科学无国界,但由中国孩子来做这件事不是更熟悉、更亲近吗?”
在数千年书海中掘金,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个人的生命就显得有限。为此,当时34岁的他,整整为此规划了之后31年的学术生涯,直到65岁,全史出齐,办理退休,默默离开。
黄天华有些哽噎,“因为‘祖国’二字分量太重,那就是我的妈妈,活在世上不能放弃自家母亲。”据目前著作研究进展情况,全书军费支出、皇室支出、官俸支出、祭祀与宗教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几项,贯穿历代各章,厚重扎实,都可独立成篇,单独成书出版。
工资几乎都用于史料和差旅
“为祖国母亲讲故事,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甚至可以没吃没喝。”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周期长,10年、20年、30年都有可能,而不太可能作为如此长期的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费可以资助,黄天华只有自掏腰包。“这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
史料价格特别贵,1986年到2014年集中撰著期间,黄天华的全部工资几乎都用于史料搜集和差旅之中,单就这部《中国财政制度史》的资料费,陆陆续续累计达19万元。
最狼狈的一次,是他去北京图书馆、财政部科研所寻找研究资料。为了尽可能少花钱,他住在50元一晚的火车站招待所。“我一学生见状,实在不忍,把我送到一个普通招待所安顿下,”黄天华回忆起,当看到一晚要200多元时,自己的心在滴血。他至今清晰记得,京沪之间车票曾经只要12元,正是他常常搭乘的13/14次列车。
他至今无法忘怀一个资助人——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校党委书记丛树海。“那时候我实在太困难了,所需资料根本买不起,只能采取复印的方法。”黄天华从来不去校领导办公室,但那次,他在楼梯口碰见了丛树海,见这位校长从口袋里掏出4000元,“说心里话,当时连谢绝的勇气都没有”。不止一个领导单独资助过黄天华,但给的钱却从来没让他签过字。“等空下来,我会算算,究竟给了我多少。”
他悄悄透露,“爱人的工资比我少,只拿3000多元,还要养家糊口,我真是不好意思从她兜里拿钱。”如今,财大毕业的女儿已独自立业,她虽没有继承父亲衣钵,选择了金融行业就业,但仍时不时“赞助”父亲的这份终身任务。
每年从大年初一到第二年的年三十晚,黄天华没有休息日,早晨5时起床,深夜12时睡,除了吃饭只睡5小时。学生们说,黄老师除了上课时间外,一般都待在自己办公室,寒暑假亦风雨无阻。所以平时深居简出,在校园里偶尔可以看到他骑一辆破旧的小电动车疾驰而过,日常穿着与生活细节几乎数十年都不变。
三十春秋如一日,黄天华的身体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 写到一半时,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1年时间治疗与调理。当时,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没有听从医生建议。后来,又陆陆续续患上肺气肿、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中国财政制度史》2015年完稿后,按规定出版费用为每10万字1.7万元,全书550万字的出版费用就高达100万元。为此,黄天华的梦再度阻遏,只得先用每套500元的价格打印了5套,报送政府部门和出版机构。经多方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定下50万元出版费,国务院规划办拿出35万元资助,校方又给了25万元。“这样多了10万,可供下一步动用,但还没动过。”黄天华说。
当铺路石帮后继者坚守下去
在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当了十多年院领导的胡怡建,也是黄天华的老同学。他深知黄天华,日常被视作有些木讷之人,不善于人际交流,也从来不参加那些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价值不大的活动。“只是经常看到他弯着腰,艰难地完成课程,疲惫地走出教室。”
在上海财大资深教授鲁品越看来,当下重论文轻著作,重项目轻成果,重短期成果轻长期积累,这成为评定各种头衔的规则。在不尽合理的规则下,黄天华这样的学者注定晋级艰难坎坷,“对于一辈子献身学术的人,若未被学术所承认,这是知识分子最难承受的打击”。
好在,学院对他宽容,评教授不用论文评,用著作评,不约而同投了赞成票。他从1978年走上财经学术之路,到2008年58岁时才终于评到正教授,而且还是破格晋升。“教授职称拿7800元,而之前副教授是5800元。”黄天华笑着说,“多了2000元,日子好过多了,因为一半以上工资可以交给爱人了。”
说来是甜,实则是苦,在多数人眼中,财经学者似乎以应用为导向。作为基础研究,史学研究的不景气是客观现象,经济制度史、财政制度史等专业史更是如此。“但我国需要有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眼下实在是太缺这类人了。”黄天华说,让他觉得悲哀的是,自己的学生几乎全都半路改道,目前只剩下钟灵娜还在坚持。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黄老师常常这么教导我们。”这位2013级财政学专业硕博连读博士生说。但黄天华深知她的不易,也不为难她。在读期间,钟灵娜发了好几篇史学论文,但最终还未决定是否干这一行,或今后改教财政学为好。
“是学生不愿意吗?我觉得不是,他们看到我太苦太苦了,所以选择了别的相对轻松、容易出成果的路。”黄天华说,自己既担心财政制度史研究这条路后继无人,又担心后来者像他一样一生清苦。“我快退休了,没有精力再去坚持,”他说,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为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生当铺路石,帮助他们坚守下去。